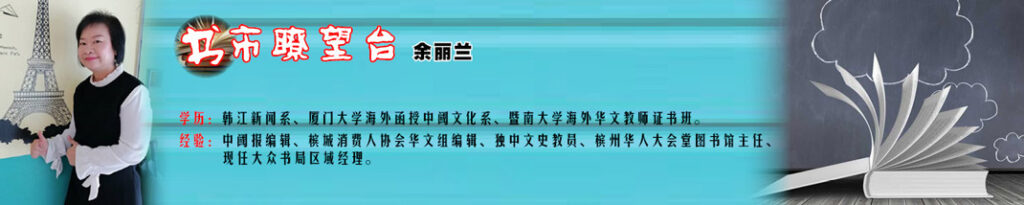
讲到才子,环顾中港台,其实屈指可数,数来数去也就两个人,一个叫陶杰,一个叫李敖。号称才子的人不少,然而,学贯中西,能出口成章,称得上文采风流者,却少之又少。陶杰,绝对是才子中的才子,童叟无欺。
陶杰原籍广西,出身左派报业世家,父亲曹骥云为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陶杰在香港湾仔长大,自幼接触古典文学,曾经于香港左派学校就读,但完全没有受到左派影响。
陶杰的作品主要使用中文写作。文笔优美,词藻华丽,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抽象的感觉和概念化为立体的景物,使笔下文字带有强烈的视觉效果。作品中常见中西文化的比较,揭示中国文化弱点和缺失。对九七后香港特区政治文化中的各种中国化现象,时常大加批评。
陶杰对中国文化认识深厚,但经常表现出崇尚欧日文化,对英国更向往不己。他有一个观点:“ 香港虽然成了“国际都市”,骨子里却仍然是中国的一条农村。”陶杰认为“九七”前香港由英国管治,英国代表西方的文明,法治,理性,而且有秩序,能够压抑中国小农社会的劣根性。

香港的文化氛围
文化大革命前后,香港有一批知识分子是从,中国南来的,他们在香港办大学杂志,保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金庸先生当初也是在一个旧楼里办《明报》,一部部武侠小说,就在风扇的摇摆下写成。中国文化要在一种压力下才能保存。
“中国文化是很丰富的,有黑道和白道,太极图也是黑白两色的,我们读唐诗、宋词、孔子、庄子的书,属于白道。下面也有一套黑道,易卜星象、功夫、黑社会、命理。60、70年代,当时中国封闭,破四旧,那些东西都象漏斗一样都流到香港来了。当时香港的人文气氛很好,到了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了,经济起飞,香港人也富有了,不大追求文化了。”
1997年香港回归,回归前香港人空虚失落,一批文化精英移民到加拿大。现在的一代是在消费泡沫中长大的,他们对文化并不是那么有兴趣,所以现在香港处于文化的断层。虽然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香港的这一代没有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文明、经济体之间竞争激烈。生于香港,长于英国的陶杰担心,香港在九七后出现经济泡沫化,人文精神走向腐败低俗,现在的香港己经没有文化氛围了,文化艺术己经移向台北还有中国大陆的北京和上海。香港己经没有“复兴”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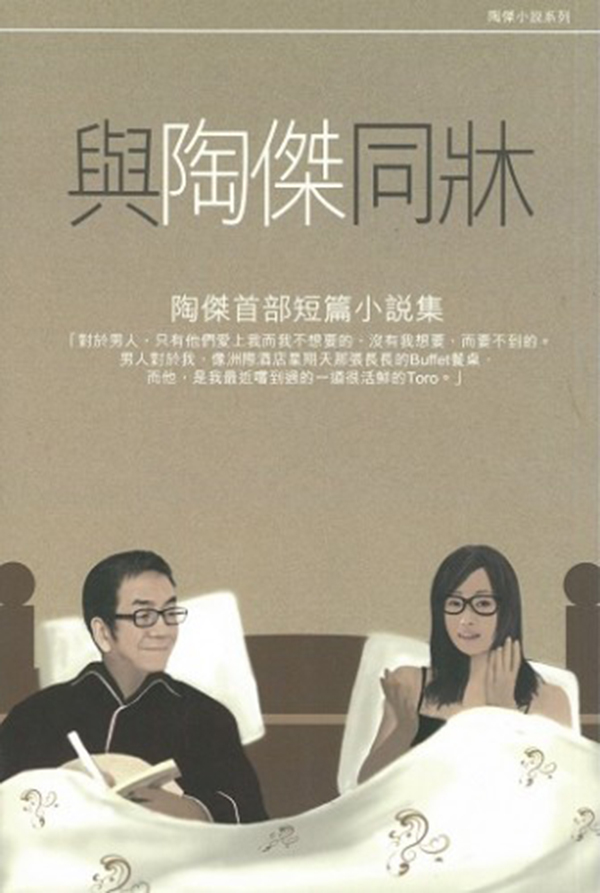 陶杰看金庸
陶杰看金庸
1993年,陶杰应金庸邀请,开始在《明报》定期发表一些随笔,后来开始撰写副刊的《黄金冒险号》专栏,共历10年。《明报》应该属于偏左的报纸,陶杰的政治观点似乎跟金庸先生的不是那么吻合,陶杰如何解读他跟金庸先生的关系?
陶杰认为金庸是一个奇才,很愿意扶掖后进。陶杰觉得很可惜的是,他认识金庸比较晚,那时金庸己经快要退休了。金庸在《明报》提拔了很多人才,像黄沾、林燕妮、蔡澜等。金庸在香港是一个很值得人尊重的企业家。眼光好,文笔好,对历史了解的透彻,写小说的才华真的是盖世。香港的文化离不开金庸,武侠小说是从香港开始的,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香港的小说,也是中国的小说。金庸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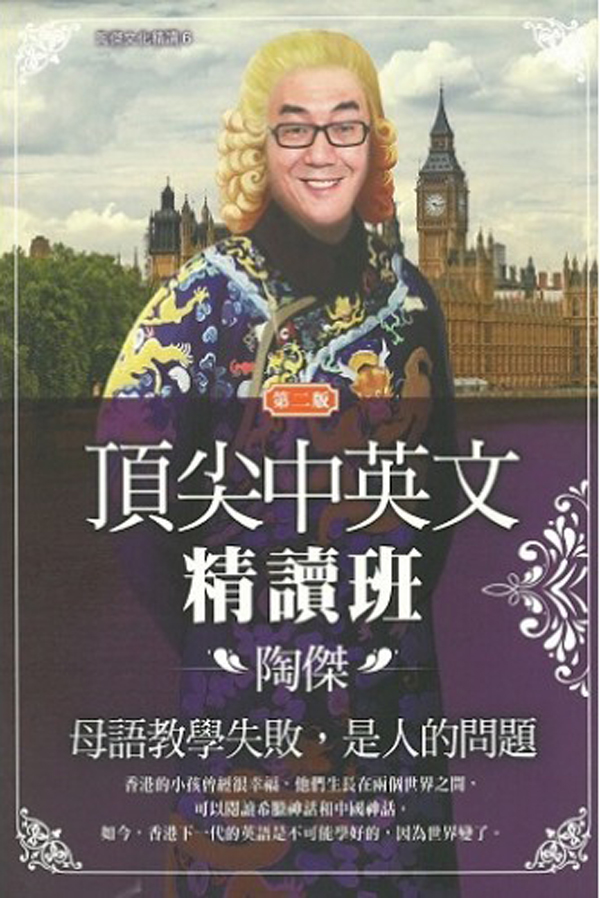
才子说情人
才子陶杰是如何定义女朋友和情人?他说:“有的女人是为爱情而生的,不是为婚姻而活的,这种女人天生就比较浪漫,追求无穷无尽的美感和快感,一旦踏上婚姻,就会稍纵即逝,不过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占少数。”
情人是一种美感,情人是不能成为妻子的,如果成为妻子,就会慢慢转化,不会再激动了。妻子,丈夫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婚姻是一种沉淀,不是升华,但是生命有不同的阶段,年纪大了,也不能够常常浪漫,在适当的年纪要做适当的事。
香港的“发展”动力是地产经济,这就决定了香港一切“古蹟”最终必然要全部拆毁的历史命运。 陶杰今次集中对文化遗产保育开刀,斥责香港以及内地政府一味只追求经济增长,不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摧毁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同时,更深情忆述了许多陶杰个人成长经验中属于旧香港和一个时代的旧物、旧人、旧情,描绘了一幅残存于经济发展车轮碾压下的最后的文化记忆地图。
“对于男人,只有他们爱上我而我不想要的,没有我想要,而要不到的。男人对于我,像洲际酒店星期天那张长长的Buffet餐桌,而他,是我最近尝到过的一道很活鲜的Toro。” 陶杰首部短篇小说集,八篇悬疑情色小说,刻划当下港男港女的故事:初出茅庐的女社工、游走中英港台的空姐,年近三十的教徒护士、公屋长大,人到“剩年”的金牌女记者,以及迷失西藏的中环OL……陶杰以他洞察人心的睿智,为你写下二十一世纪最残酷又感性的人性斗争录。
陶杰独具一格的“骂人艺术”——鞭辟入里、生动形象,令读者忍俊不禁的同时又大呼过瘾。无论喜欢陶杰与否,无人能否认陶杰是当今香港文坛“最会骂人”的才子,在香港社会矛盾日益紧张、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集体发洩”的今天,香港仍需要“敢骂、会骂、永远在骂”的陶杰。
继《上等英文词典》、《高等中文大典》、《头等英文金句录》后,再度对“病态”中英文开刀,一手感怀优雅中英文传统跟美好时代的一去不返,一手将被现代化跟网络化荼毒的劣质中英文揭露得体无完肤,扒皮露骨地从中抽出语文教育的劣根性和专制统治思维的罪恶。








